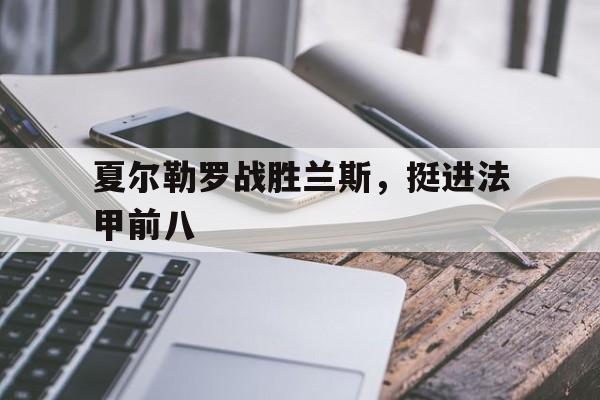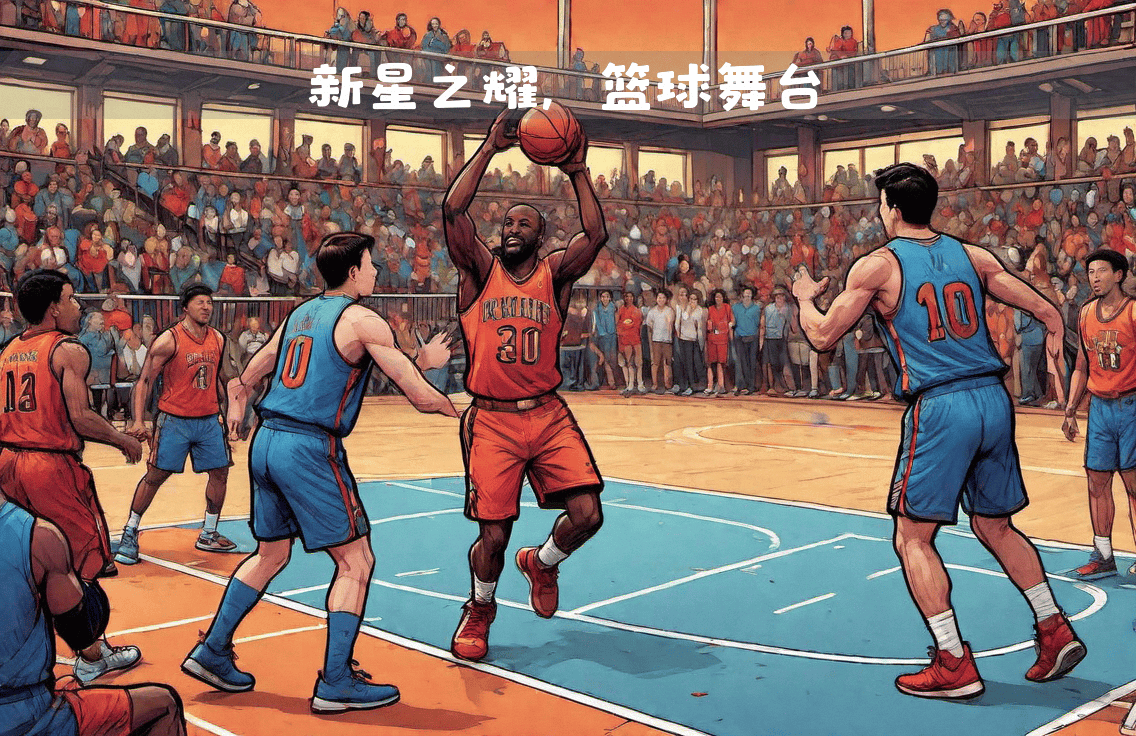腾讯公益的“小朋友”画廊曾经在朋友圈掀起热潮,相关组织提供了一系列精神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患者的画作线上展示,吸引了不少关注。踯躅于寻常生活中的人们,一方面为作品的绚烂与美丽讶异、感动;另一方面又与面对所有公众事件时一样,提出了一些质疑:画作是否真正出自患者之手,绘画天赋总能伴生于其他障碍吗?如果这波热议,能与《尼斯:疯狂的心》上映同期,或许会有助于后者票房,也将提示观众,以更温柔与深入的方式,理解主人公及其推行“艺术疗愈”的思路与核心。
《尼斯:疯狂的心》作为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继《海边的曼彻斯特》之后引入发行的第二部外国电影,讲述了巴西女医师尼斯(Nise da Silveira)探索精神病治疗方法的经历与故事。她曾是医学院唯一的女学生、精神病治疗粗暴当道时少有的抵抗者、因共产党身份遭受管束的异见分子以及将荣格分析心理学引入巴西学界的重要人物。
影片节选了这位传奇女性上世纪40年代在医院自创一方自由天地,为病人打造艺术(尤其是绘画)工作坊的相关经历。而摄像机,则捉住了巴西国民女星格劳瑞·皮尔丝坚韧脸部线条下的母性象征与温柔方式。随之,女性的温柔与艺术疗愈的“温柔”在她的小天地内达成一致,而精神病患者被隔离的处境,与女医师被排斥的境遇,似乎也划归同一阵营。电影的大部分段落相当唯美和煦,譬如精神病人出外郊游写生,抑或在庭院中轻声细语。纪录片出身的导演罗伯托·柏林厄以手持摄影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纪实风格,又以相对浪漫优雅的方式来重现这样的回忆。而那些与温柔相对的关键词,诸如冰冷、僵硬,甚至电击,则属于当时,或者说直到如今,仍占上风的男性权威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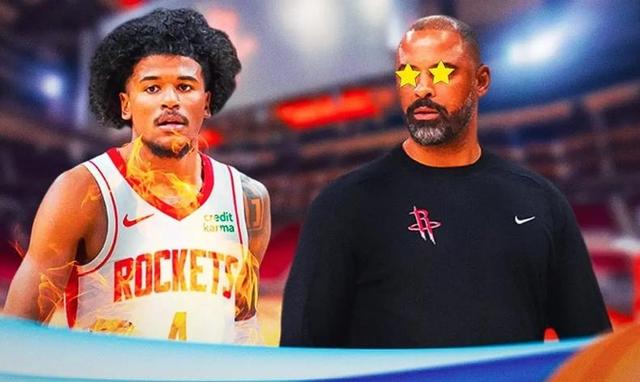
在感性的氛围与温和的影调里,我们没有被影像绑架去观赏一个斗士充满张力跌宕起伏的一生,而是与轻和音乐、与尼斯一起,陪伴病患寻求相对平衡的宁静生活,并且发现他们无意识画作中潜藏的心理规律与精神价值。真实生活中的尼斯,后来创办了无意识图像的博物馆,电影中,她也在病院举办画展,为观众导览绘画创作演变中的细部逻辑。
“优雅”应该是这部电影最突出的关键词,它以极其精致的打光,给予影像中的时光一种珍重之感。影片中,病患的扮演者既有演员,也有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他们几无表演痕迹,在狭小空间中漫游时,无夺人眼球之举,却妥帖呈现了神游太空、难以自控的跌宕状态。表演的留白里,更能渗漉其个人史中的复杂情感,对自然、对世界的观察体认。从片尾的真实影像中,我们可以揣测,导演参考档案,有意识地复原了尼斯与患者共同生活的场景断章。

《尼斯:疯狂的心》是一部传记电影,传记电影佳作颇多,却也有被人们谙熟了套路。《尼斯:疯狂的心》在“套路”一点上有所争议,有人认为她中庸,没有逃出传记片的“优良”气质,又有人嫌弃平淡,沉迷于带有梦幻色彩的人性博爱。但如此论断似乎都是出于影片与期待的差异。然而,跳出传记片模型,或许还有其他切入可能,来判断其人物营建、主题表达的成功与否。
印度裔大导演塔西姆·辛在好莱坞曾拍摄过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近未来故事,名叫《入侵脑细胞》,由詹妮弗·洛佩兹主演。美貌的儿童临床医学家应用高科技手段,进入病人梦境,以求解开根植童年的心魔,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让病人反向进入她的大脑,从新的环境中,获取战胜分裂邪恶人格的能力。塔西姆·辛把梦境幻想的每一个镜头,都引经据典,拍出了现代艺术经典的架势。电影中,实际具备情感张力的,与其说是侦探探案的情节,不如说意涵复杂的画面构图。我们从鲜明的视觉风格,直接看到了人物内心的冲突与混乱。
对照尼斯,她与精神病患,其实也是在交换彼此的情感世界。她的心灵,是阳光摇曳的庭院理想国,而病人的精神之门,则恰恰存在于无意识绘画的“方圆”之中。精神分裂者在疯狂躯壳里保有灵锐,尼斯健康的肉体里,却是一颗真正的疯狂心,为学问、为责任、为理想、为人类。
精神治疗法的激进与否、粗暴与否,不只是将病人当作问题,给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而涉及更本初的观念,例如精神分裂者是否完整人类,是否有权与我们享受同样态度的对待。影片最后,画作体现了“传统精神病学正在扼杀的东西”此一说法终于奠定,而那些曾经被苛刻对待如同野蛮动物的患者们,获得了“巴西新兴艺术家”的称号。真实的尼斯,垂垂老矣之时,仍不忘对摄影机背后的观众反复叮咛:“有一万种方式去活出你自己,为你的时代而奋斗。”《尼斯:疯狂的心》最打动笔者的,正是在纪实中实现了交融共生的抽象情境。其平常并非贫瘠、中正而非中庸。它用艺术之美观照生命之美,用自然之美提示生命之间理应平等。可以说,它所讨论的事物,实际上在精神治疗之外,含括了更大范围内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观念。
无论作为葡语电影、巴西电影、女性电影抑或精神疾病题材电影,《尼斯:疯狂的心》都是国内院线罕见的一部作品。但话题未热之时,这些关键词恐怕无法在任何宣传渠道中为这部影片增添吸引力。观看《尼斯:疯狂的心》的过程,绝对不是艰涩,或不甚愉快的体验。它用诗意包裹人性关怀,用悠扬淡化残酷压制,是一部完全没有观看门槛的电影,也确实有效于各种社群的观众。讨论或许不容易发生,但那些摇摆的叶影和晃动的光线,可以感官细节的形式长留,于走出影厅的观众而言,或许类似于羽绒服包裹里不急着散去的温度。
文| 张耀婷
本文刊载于20180202《北京青年报》B7版